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,去中亚拜访沉默的邻人|此刻夜读
九年中的许多次,作家刘子超数次深入亚洲腹地,前往神秘的邻人之国——乌兹别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——展开一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寻觅之旅。
作为亚欧大陆的中心,曾经“丝绸之路”的驿站,中亚在当下成为我们面目模糊的邻居。为了深入中亚,作者学习当地语言,研究路线和历史:驰骋核爆场和无人区,见证未知之地;重走“丝绸之路”,跟随玄奘足迹,感受时间流逝;与普通人交谈,倾听财富、迷失、困守的故事——通过文学、历史和个体故事等多维度视角,见证陌生之地的流动现实,寻找世界的失落之心。
2018年,中亚作品入选单向街“水手计划”项目;2019年,经评委梁鸿、吴琦等人推荐,书中乌兹别克篇章入围由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的“全球真实故事奖”(True Story Award),获评“特别关注作品”,这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甄选、由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参与的非虚构特稿大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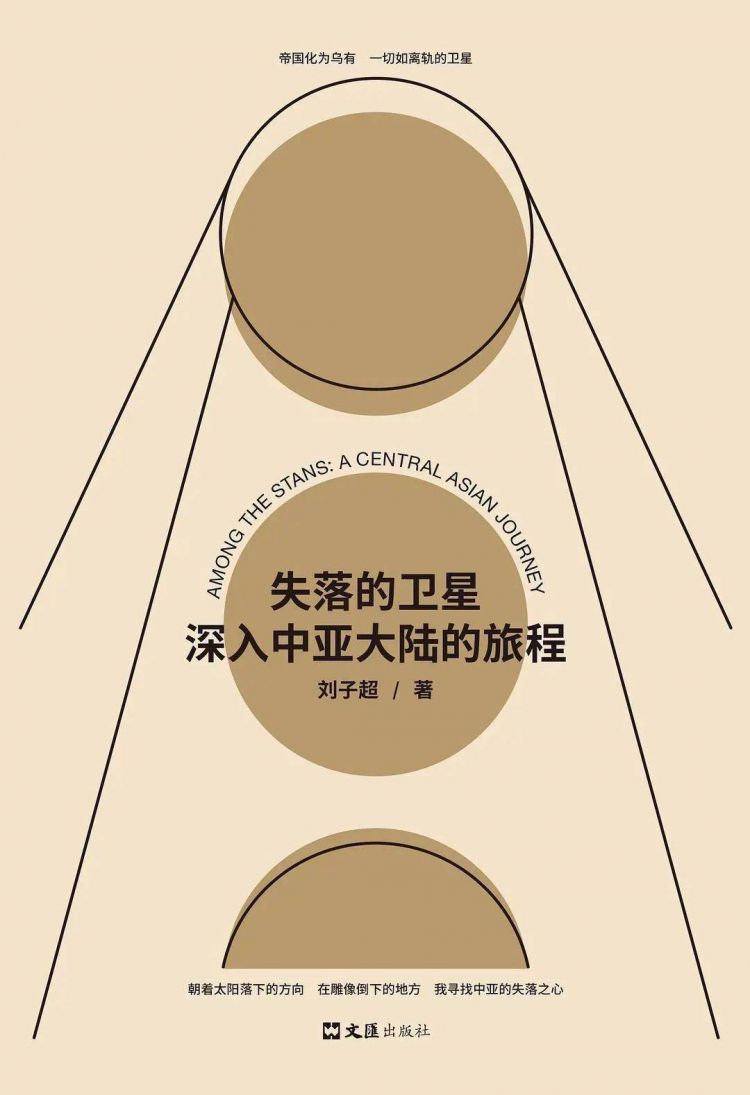
《失落的卫星: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》刘子超/著,新经典·文汇出版社2020年7月版
今天的夜读,为你带来由新经典推出的《失落的卫星》一书中“天山游记”中的片段,“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,在雕像倒下的地方,我寻找中亚失落之心。”

天 山 游 记
刘子超
我把大件行李寄存在旅馆,告诉老板我几天后回来。我随身只带了一个背包,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、雨伞、瑞士军刀、一小瓶吉尔吉斯斯坦牌白兰地,还有一本谢苗诺夫的《天山游记》。
出发的清晨下着小雨,天山笼罩在一片云雾中。我坐着乡村小巴来到阿克苏,穿过寂静的村子,向着山谷深处走去。山间飞起漫天的乌鸦,仿佛一场大火后被风吹起的灰烬。它们怪叫着掠过灰色的天空,纷纷扬扬地落在一片草坪上,然后雕塑般定格在那里。
山谷中是急促的卡拉科尔河,泛着白色浪花,像鼓声一样响动。山谷本身则是美妙的:到处是云杉、圆柏和花楸树;草地上开满紫色的薰衣草和白色的忍冬花。

天山-阿拉套
开始时,道路较为平坦,但很快就变成难以下脚的卵石路。那些被河水冲刷的卵石有大有小,很多时候甚至需要手脚并用,才能爬过一段险坡。
最初的一个小时,我没遇到一个人,只有我独自走在大山深处,周围是还没有被征服的风景。不久,天色变得越来越暗,山谷里阴云密布,隐隐传来滚动的雷声。
第一滴雨点落下来的时候,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。阴云在头顶缭绕,空气中饱含着水汽。雨水像游牧民族的大军,成批地落下来。气温顿时骤降,即便穿着外套,依然寒气逼人。山间的树林变得更加幽暗,河水翻滚着冲击石头,掀起巨大的浪花,声音也似乎更响。
雨很快呈瓢泼之势,山消溶在远处,一度甚至看不清眼前的道路。即便我撑着雨伞,也无法阻挡被寒风裹挟的雨水,从伞下面钻进来。我加快脚步,希望身子能暖和起来,更希望尽快到达落脚之处。我始终留意着路上有没有马粪,有马粪就说明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前面——虽然不知道还有多远——有吉尔吉斯牧民,有住处,有食物。

采棉女工
一个徒步的外国人迎面而来。直到十米之内,我们才在大雨中互相看到对方。他是专业徒步者,装备齐全,背着大行李,穿着防水夹克。雨水顺着他的大胡子滴滴哒哒往下淌。长时间的艰难行走,让他的面容变得严肃而沉默:他瞪着眼睛,紧闭着嘴唇,仿佛一个受难者。我们点了一下头,然后在山路上错身而过。
我转过头喊:“到阿尔金—阿拉善还有多远?”
他也只是喊了一声:“很远,至少还有五个小时。”
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。这只能说明,在大雨中徒步,让我丧失了时间观念,也大大降低了速度。晴天时,这条路需要六个小时,但在雨中变得无法估测。
渐渐地,走路变成一种机械运动。我甚至感受不到冷,也无所谓雨水的肆无忌惮。我的鞋和衣服早就湿透,这让打伞的行为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可笑。我一直在向上走,不时绕过山丘。我时常幻想,下一座山丘背后就是开阔的阿尔金-阿拉善山谷。正是这样的幻想,维持着我的机械运动。我也幻想着一顿热乎乎的午餐:大量的碳水化合物、热茶、我的白兰地。在《天山游记》里,谢苗诺夫写过他的晚餐——羊尾油煎泡软了的黑面包干——听起来真好。

苦盏的锡尔河畔
五个多小时后,一片绿色的山谷终于在我面前打开。远处有一片白色的蒙古包,宛如海市蜃楼。一个牧民家的男孩骑马跑过来,见我一身狼狈就邀我上马。草地已经吸足雨水,成了一片小沼泽,马蹄踏上去噗嗤噗嗤响。男孩把我送到河边的定居点前,只见河岸高处的空地上,散落着几座蒙古包,还有一栋冒着炊烟的木屋。
听到马声,一个吉尔吉斯男人从木屋里走了出来。他穿着夹克,戴着帽子,脚下是一双沾了泥的登山鞋。他把我迎进木屋旁边的“餐厅”——那是一个用防水塑料布围起来的空间,里面摆着木桌和长条凳。他说他叫穆萨,是这家客栈的老板。他手下还有一个帮工,兼做厨师。厨师戴着小帽为我送上一壶热茶,又端上一盘抓饭。雨已经停了,空气依旧湿冷,山谷内升起一团白雾。
见我一副很冷的样子,穆萨指着河对岸的一个小木屋告诉我,那就是泡温泉的地方。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,我拿着穆萨给的钥匙,跨过一座小桥,走到木屋前。所谓温泉,就是在泉眼附近挖了一个蓄水池。泉水不停注入池中,溢出的水则通过排水管流进河里。温泉有股硫磺味,冒着轻微的气泡,我半躺在池里闭上眼睛,耳边只有卡拉科尔河的流水声。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,温泉如同上天的馈赠。

《哈气河马》插图
等我回到穆萨那里,他正坐在餐厅的长凳上,拿着望远镜窥视对岸的人。穆萨不好意思地放下望远镜,嘿嘿笑了一声,说带我去蒙古包。他把铺在蒙古包穹顶上的羊毡扯掉,让光线从上面洒进来。他又抱来一捆木柴,在炉膛里升起火。炉子很快热了,我把湿鞋放在旁边烘烤。一串白色的水汽瞬间腾起,鞋子发出呲呲的响声。
蒙古包里暖和起来,我一边小口喝白兰地,一边阅读《天山游记》。1857年第二次天山旅行时,谢苗诺夫也到过阿尔金-阿拉善,也在靠近温泉的地方安营。
当时温泉的木门上有保存完整的藏文题词。泉水同样流入一个长二米、宽一米、深一米的水池,池子的四周由花岗岩围着。他测量出的水温是四十摄氏度,而营地的绝对高度是一千八百一十米。他写到自己的兴奋,因为这是他“深入天山中心遇到的第一条山谷”。在一盏油灯下,他开始写日记,把当天采集到的珍宝——外伊犁高山植物群的稀有植物——夹在吸墨纸里。

测量塔
傍晚时分,我合上《天山游记》,走到蒙古包外。那位厨师正跪在空地上祈祷。他告诉我,他的祖上是陕甘地区的回民。同治年间,陕甘回变,一批回族迁徙到中亚,很多就定居在伊塞克湖地区。他夏天来这里帮工,冬天回到卡拉科尔。他的老婆孩子都在那里。

养鲤鱼的渔民只剩下最后一户
说话间,我的蒙古包里又住进两个从卡拉科尔徒步过来的旅行者。他们是瑞士大学生,女孩叫莫妮卡,男孩叫尼古拉。他们似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侣。短发的莫妮卡似乎在关系中扮演着男性角色,尼古拉的举手投足则有些女性化。
他们洗完温泉回来,一边晾着头发,一边商量第二天的行动。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附近的高山湖。他们听说,徒步到那里只需要三个小时。
“应该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散步,”尼古拉说,“你可以和我们一起。”
睡觉前,我从外面抱回一捆木柴,手上全是松木的清香。我把炉火烧旺,除了门口附近的烂泥,别的地方都开始变得干燥。尼古拉脱掉外套,只剩一件松松垮垮的内衣。他把眼镜折起来,放进眼镜盒,塞在枕头下,把身子陷在褥子和毯子的坑里。睡在旁边的莫妮卡穿着一件男士背心,翻着一本瑞士人写的旅行文学——《世界之道》。
炉火噼啪作响,但红光会渐渐暗下去,越来越暗,直到我们被黎明的轻寒冻醒。
新媒体编辑:金莹
配图:文中配图由出版社提供
相关文章
-
为何八戒被貶成猪,而老沙还是人样?玉帝:很公平!不可同比而论
-
国内综艺抄袭又出新套路——号称买版权,实际不给钱?
-
《西游记》开篇构建了一个新世界,孙悟空才是最闪的辰星
-
为何老君烧不死孙悟空,如来只敢压五百年?因为有人罩,不是菩提
-
揭秘观世音菩萨传道的道场
-
斥资1亿耗时7年,这部电影上映2天遭下架,六小龄童也很无奈
-
玉鼎真人是孙悟空师傅吗 宝莲灯中是孙悟空师傅(实际上不是)
-
《西游记》拍摄花絮,杨洁客串小妖,孙悟空大战六小龄童
-
孙悟空和他的如意金箍棒
-
英国使团两次访华,不愿行三跪九叩之礼,清朝皇帝很生气,后果很严重!
-
黄狮精为什么被打死?只因一时贪念(偷了孙悟空三兄弟的武器)
-
神话故事后羿射日 天空中出现十个太阳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祸
-
孙悟空在变化上,不是二郎神的对手,原因在哪里?
-
王三:为什么西天取经遇上的妖怪,都不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当回事
-
杜贵晨:章回小说叙事“中点”模式述论——《三国演义》等四部小说的一个艺术特征
-
猪八戒为何与孙悟空不睦,而经常在唐僧面前搬弄是非?
-
征稿丨100个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案例,总有一个你去过
-
《西游记》中唯一吃过唐僧肉的妖怪,孙悟空和猪八戒联手都打不过
-
神话故事之羿杀的六怪兽分别是什么
-
红枣的来源 金童玉女偷吃枣的故事
-
十个太阳的神话故事:传说中后羿如何射九日解救普罗大众的?
-
移山大圣——狮驼王 狮驼王简介
-
三圣母有哪几位 三圣母与玉皇大帝是何种关系
-
揭秘: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为为何只剩半部
-
太上老君九大法宝,混沌初分,天开地辟,其一分阴阳
-
许逊审猪的故事 许天师神断案的传说
-
关于铸就连云港精神的几点思考
-
何瞻谈中国古代游记文学
-
战神刑天怎么死的 战神刑天的作战武器